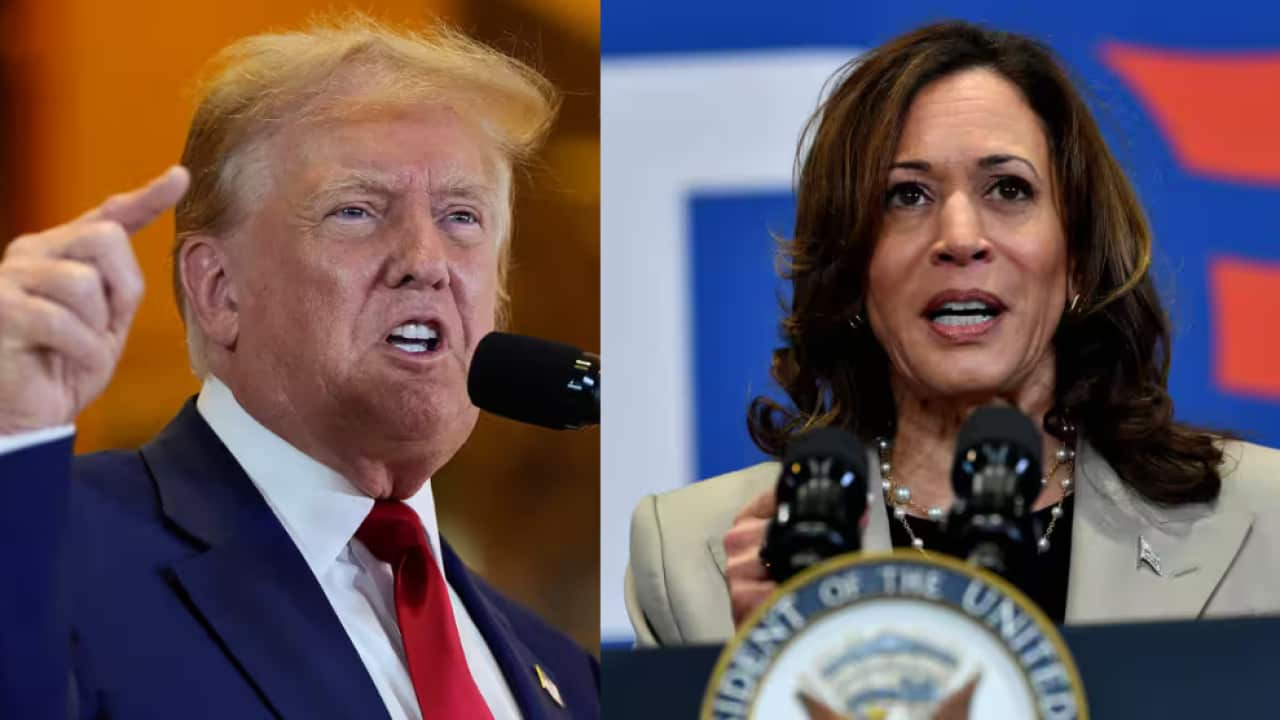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,
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
你不必訝異,
更無鬚歡喜
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。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,
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,方向;
你記得也好,
最好你忘掉,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!
— 徐志摩《偶然》。
人在一生中要擔噹多種社會角色,我們可以是相濡以沫的家人,志同道合的好友,風雨共濟的同事,或者所有以上美好的相反面。
微笑、讚美、共情、傾聽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,我們在遵循著這些雞湯式的訓條努力去維持每一段人際關系的同時,不禁要問:我們又是為了什麼要和人去交往呢?情感所需,還是名利所惑?
北宋理學家程頤說過,"鄉民為社會"。意思就是指眾人會合、結為社糰。從最早的載歌載舞慶祝豐收到祭祀,社交活動的意願按照史雙元老師的說法,最初都是情感性,而非功能性的。更多的是為了聯絡感情,不是功利。
說到社交,在社交場合找誰說話,多一點少一點,深一點淺一點,如何禮貌得體結束對話,都是讓陶敏博士感到困惑的地方。他認為,眼下一些人所定義的“無效社交”本身就是一句很功利的話。這句話本身就把社交功利化了。用“資本”來定義人的力量對比,不如用“品味”作為社會交往的標準。
從《日出》中的“交際花”陳白露,嘉賓們更是將話題延展到了對於如今又大熱的一個詞“名媛”的熱烈討論。想知道談了些啥?歡迎收聽《文化苦丁茶----社交應該是情感性的,還是功能性的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