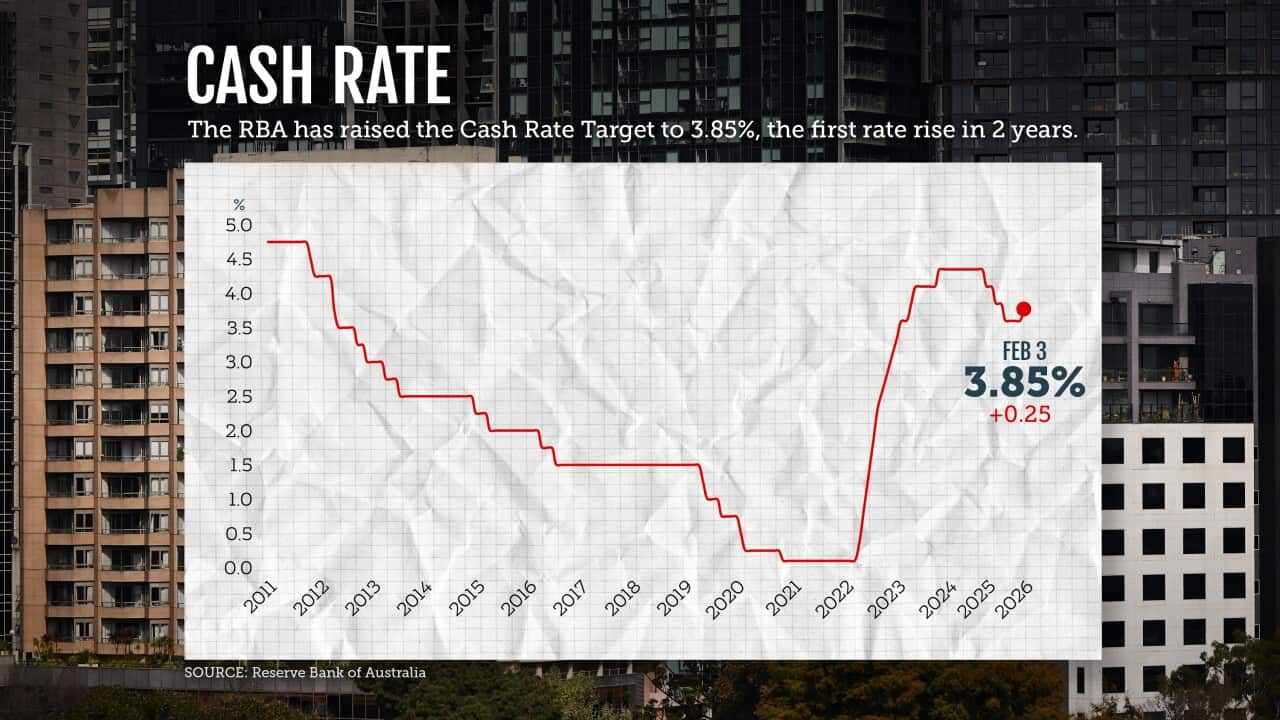点击 ▶ 收听播客。
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大提琴家之一,秦立巍(Li-Wei Qin)活跃在国际舞台已有数十年。
近日,他携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重返墨尔本,与墨尔本室内乐团合作演出。
在接受SBS普通话专访谈及这首年少时期便开始练习的作品时,他坦言,失去探索与冒险精神的音乐家就像“一身班味的上班族”,而自己更希望跳出舒适区,在同一部作品中挖掘“新的语言、新的情感”。
“以前看到蓝色可能是海洋,现在看到蓝色可能是天空……每一个蓝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
“老朋友海C”:从少年炫技到深情对话
秦立巍第一次学习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时,只有十三岁。
那时的他,更看重的是技巧的挑战和舞台上的表现力,特别是第三乐章的快速段落,是少年展示自我的方式。
然而,多年后再演绎这部作品,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。
“可能现在我的速度比当年更慢,但我更在意的是音色和语气,希望观众能听到音乐的呼吸。”
在他看来,这部作品就像一位“老朋友”,每个阶段都会带来新的启示,“从七岁到七十岁,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”。
他还提到,这部作品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大提琴学习的“必修课”之一。
“昨天我在墨尔本听到一位十四岁的学生演奏,在中国大陆甚至有九岁十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拉这首曲子。”
对他来说,这正是海顿音乐的魅力所在:既适合早期学习,又足够深邃,让成熟演奏家不断回望。
而对于经典作品的频繁上演,秦立巍坦言,最大的挑战是避免失去新鲜感。
最怕的是演出变成惯性,像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。
因此,他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——哪怕尝试未必成功,也要走出舒适区。
秦立巍将音乐演奏形容为在浅海行走,倘若一直“脚踏实地”,反而“拿走了音乐本文本身的魅力”。
“我们本来就是瞬间艺术,是在动态环境下创造艺术。我希望是走到脚碰不到地面、离开地面一点点,恰恰这个时候,是音乐创造最有魅力的时候,”他说。
室内乐:舞台上的默契与冒险
此次与墨尔本室内乐团的合作没有指挥,舞台上的互动更像是一场即时的对话,“少了一个参照,也多了一份自由”。
他说:“我个人觉得拉室内乐,运用的器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平时拉大协奏曲当然也要听,然而为了要把声音铺遍给整个大音乐厅,手指能力要求很高。”
“但是我们在拉室内乐的时候,耳朵更加重要。一个人的反应、敏锐度非常重要。”
秦立巍形容,与室内乐团的合作像跳探戈,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需要即时回应。
正是这种不确定性,让音乐保持了鲜活。
与老朋友们的再度合作,也让他倍感亲切,不仅是音乐上的交流,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
“在室内乐团里,大家像在独木桥上一同前行,每次演出都不可能完全相同。大家都敏锐又亲密地在这个对话般的环境中,共同为听众呈现音乐的魅力,”他表示。
艺术不是快餐:音乐需要时间与沉浸
秦立巍坦言,自己曾短暂离开音乐去读商科,但最终回归大提琴,并给自己设定了四年目标——练琴、比赛、寻找经纪公司。
“离开音乐反而让我意识到,这是我真正热爱的事业。”
在他看来,音乐属于艺术,而非快餐式的娱乐。
“娱乐是短暂的,比如刷手机视频只停留几秒钟;但艺术需要时间,需要沉浸。哪怕是一幅画,也可能需要你静静坐下十几分钟。这就是艺术和娱乐(的区别)。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都需要艺术,也同时需要娱乐。”
他表示,自己的工作是创造艺术,而他认为音乐艺术“应该是引领,而不是迎合”。
“音乐有很多不同类型,古典音乐,它当然也有娱乐的一些因素在,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以艺术形态为主。这才是一个古典严肃音乐家应该追求的。”
而从观众的角度而言,秦立巍认为,有些观众欣赏音乐的角度过于务实,甚至有些功利。
他打趣说,有些学生家长带孩子去音乐会,只关心上半场的协奏曲,因为孩子正在学,至于下半场的贝多芬、布鲁克纳交响曲就不太在意了。
但在他看来,音乐不能只挑“有用”的部分。
他指出:“你得把整场音乐会都听进去,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。有时候,你可能觉得某些曲子跟你没关系,但正是在这些‘无关紧要’的地方,你可能会意外发现一块钻石。”
点击此处,了解更多关于SBS如何应用人工智能(AI)的信息。
欢迎下载应用程序SBS Audio,订阅Mandarin。您也可以通过YouTube、Apple Podcasts、Spotify等平台随时收听SBS普通话播客,在 YouTube, X , Instagram,微博和微信平台关注SBS中文,了解更多澳洲新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