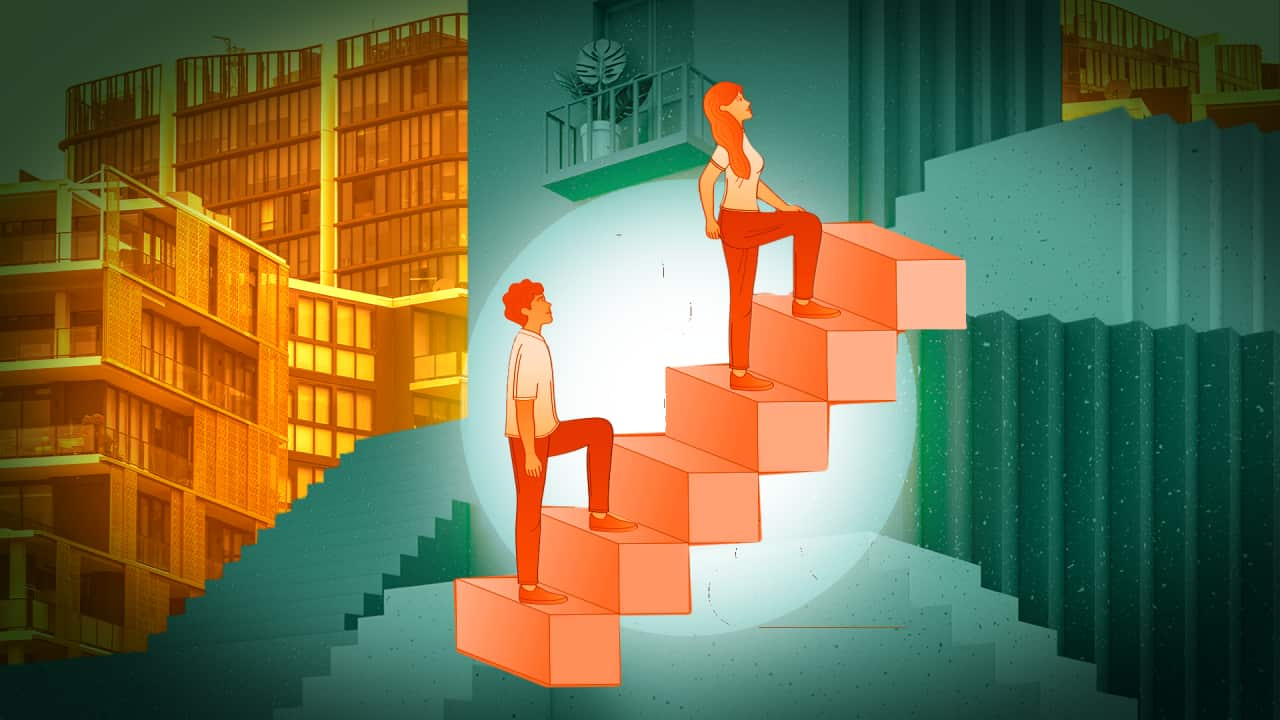要点:
- 越来越多成年人因网络共鸣走上ADHD正式确诊之路;
- 各州正尝试让全科医生开药以缩短等候、降低诊疗门槛;
- 华人等移民群体受语言与文化影响,更易延迟就诊与治疗。
点击 ▶ 收听播客。
在澳大利亚,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(ADHD)患者数量不断增加,但诊疗流程复杂、等候时间长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,仍让许多人难以及时获得帮助。
近期,新南威尔士州出台政策,尝试让更多经过培训的全科医生(GP)参与诊疗,为患者提供更便利的选择。
然而,这种“下沉式诊疗”模式在澳大利亚许多地区仍待普及。
在墨尔本,全科医生刘清武坦言:“我们没有统一标准,是否接诊取决于医生个人自信程度。”
他所在的诊所每月仅接收1至2例ADHD疑似患者,多数仍需转介至专科。
而西澳华人Ella*作为成年患者,确诊总计花费达1500澳元,其中也经历了全科医生问诊、转诊预约、自填量表等等繁琐的流程。
从“赛博确诊”走向现实诊断
在社交媒体上,越来越多年轻人自嘲为“赛博确诊”:刷到相关短视频或帖文后,怀疑自己患有ADHD。
在西澳留学工作的年轻华人女性Ella,就是这样走上了从怀疑到正式确诊的过程。
Ella最初是在社交媒体刷到ADHD相关视频后,第一次对照症状产生共鸣。但起初她并未行动,仅是默默关注。
直到后来,她在另一中文社媒小红书上读到更多详细的帖文,才开始怀疑自己有80%的可能是ADHD。
然而,一开始Ella却并没打算就医:“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ADHD……(而且)费用还是蛮高的。”
“赛博确诊”一年,最终让她下决心寻求治疗的原因,是日常生活中接连出现的风险与困扰:做饭忘记关火、工作中频繁失误,甚至影响到人际关系。
一次偶然,她的房东建议她尝试小剂量药物,那一刻,Ella形容自己“一下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”,这让她更确定需要正式确诊。
澳洲正式诊断流程并不轻松:她花了约1500澳元,随后每月药费约90澳元。
但在确诊与用药后,她明显感到生活更有条理,工作失误明显减少,也有了备考英语的信心。
与此同时,她也不再强求他人的理解。
“没有确诊前我是比较希望男朋友能理解我的,但他一开始觉得我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ADHD的症状,是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。但现在我服药后生活状态变好,能够理解自己和同样患有ADHD的人了,所以我不太要求别人能够理解我了。”
Ella感叹,网络讨论让她第一次有了“被理解的感觉”,但她也承认并非人人刷几条视频就一定是ADHD——医生在问诊过程中,也会询问Ella很多小时候的经历,比如学习情况、老师评价等,确诊不能只靠自我感觉。

对于仍在自我怀疑的人,她想说:“真的可以去看看,不要一直拖下去,就算不是ADHD,也可能是焦虑或其他问题,及时确诊或者做一些心理疏通,对自己是有好处的,不要放弃。”
等待、成本与面子文化:就诊路上的障碍
如今,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,想要拿到ADHD处方药,患者必须先经过精神科或儿科医生正式确诊,并由专科医生首次开药,然后才可能让全科医生(GP)跟进续方。
这一流程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、数月等待期,也让不少患者因此止步。
Ella说:“我当初意识到有 ADHD 的时候,其实还是有一段比较痛苦的时候,因为又不能马上去确诊,因为价格比较高,还有就是因为不能服用药物,所以我觉得还是蛮痛苦的。”
维州全科医生刘清武接受SBS普通话采访时分享道,当前体系对GP来说确实有现实障碍。
他说:“ADHD(的诊疗)在维州没有明确的规定,如果医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,没有信心接诊ADHD患者。他可能就会把患者转介给专科医生去了。”
刘医生坦言,如果维州也能让感兴趣并接受培训的GP直接诊疗,“肯定能减轻精神科医生负担,也能帮到更多患者” 。
对于华人移民群体,刘医生指出,文化认知差异与“面子文化”往往让患者讳疾忌医.
“有些家庭觉得谈精神类问题不好意思或没面子,就算怀疑孩子有ADHD,也倾向先自己观察,没有咨询意识。”
语言也是一大障碍——移民家长或患者如果英语水平有限,面对一堆英文诊疗材料和漫长的医疗流程,更容易拖延就诊。
他总结道,其实ADHD并不可怕,只要早诊断早治疗,是完全可以控制和改善的。
但他也提醒,社交网络上关于ADHD的讨论让一些人出现“自我筛查”甚至“过度担忧”的现象。
“自我筛查有一定帮助……但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(导致了)自我担忧,因为网络信息毕竟不是很准确。”
刘医生建议,将网络获得的信息作为提醒,而不是结论,最终仍要交由专业人士评估。
成人ADHD用药率翻倍 政策改革呼声渐高
近年来,各州逐步尝试“下沉式”改革,让经过培训的GP直接参与ADHD的诊断与处方,以应对精神科医生不足、患者排队压力的困境。
新南威尔士州将于今年9月启动第一阶段改革,允许接受专业培训的GP为已确诊患者续方。
而2026年,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:让接受额外培训后的GP具备诊断与开药的资质。
昆士兰州早在2017年,就允许部分GP为4至18岁的儿童诊断ADHD并处方药物,但成人仍需专家介入。
西澳州也在加紧改革的步伐,政府表示将资助培训首批65名GP,预计2026年后,这部分医生能直接为10岁及以上的患者诊疗。
此外,南澳州、塔斯马尼亚州和首都领地也提出,将在2025至2026年间开展类似试点。
然而,维多利亚州至今仍保持传统模式,GP必须将患者转诊至精神科或儿科医生确诊后,再跟进续方。
但当地也有医生呼吁借鉴新州第二阶段改革的做法,缓解患者负担。
近年来,澳大利亚成人ADHD的确诊率持续攀升。
根据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(AIHW)最新数据显示,2023至24财年全澳ADHD相关处方量达460万次,涵盖约59万名患者,处方率为每千人中有22人使用ADHD药物,是2004至05财年时期的11倍增幅。
此外,成人患者(18岁及以上)人数在2022至23年已接近21万人,首次超越儿童患者数量 。这一趋势反映出越来越多像Ella一样的成年人,在网络信息和生活体验双重印证下,最终走进正式诊断路径。
面对这一迅速增长的成人患者群体,澳大利亚全科医生行业协会(RACGP)与ADHD 专业组织纷纷呼吁,应扩大GP的诊疗权限,设立全国统一的开药标准,并加强对GP持续培训与支持。
全科医生行业协会指出,一体化、可及性强的初级诊疗体系,有助于缓解精神科医生资源短缺、缩短患者等待时间,同时为成年患者提供更及时的帮助。
澳大利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组织(ADHD Australia)也正在推动全国框架的制订,以实现更早诊断、更科学治疗和更公平保障。
(*为保护受访人隐私,此处为化名)
欢迎下载应用程序SBS Audio,订阅Mandarin。您也可以通过YouTube、Apple Podcasts、Spotify等平台随时收听SBS普通话播客,在 YouTube, X , Instagram,微博和微信平台关注SBS中文,了解更多澳洲新闻。